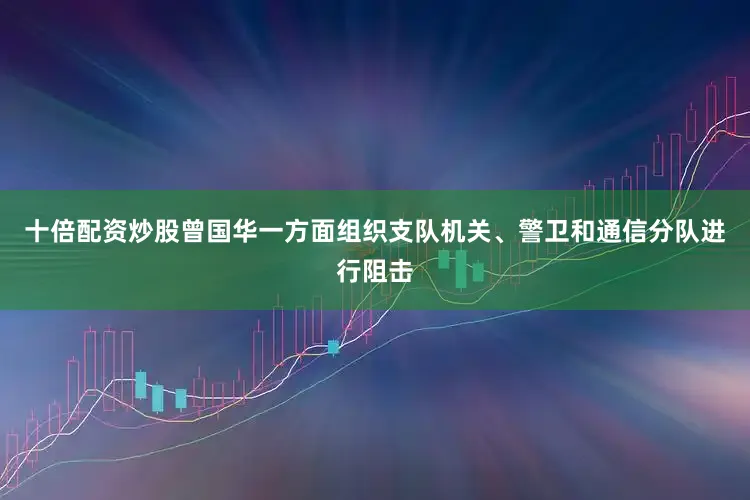
在冀鲁边平原,一场激战正酣,大宗家奋力突围,其英勇之举,竟将敌军首领山田大佐击毙,消息传至东京,震惊了整个日本。

开国中将曾国华在其所著《思想历史自传》中回忆道:“1939年春,武汉沦陷,敌军回师对我边区进行‘扫荡’,自此,边区斗争愈发紧张,敌军‘扫荡’行动日益频仍,部队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斗状态。得益于游击战术的正确运用,我们在反‘扫荡’中屡获胜利。然而,随之而来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轻敌麻痹思想,导致了我们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损失。在开辟德平、陵县地区的过程中,我们于大宗家驻防,一举歼灭了千余汉奸,并在两次‘扫荡’中成功抵御了敌人。此后,为了建立政权机构,我们在一地长期驻扎,却未能准确掌握敌情,结果遭到敌人突袭,部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华北日军启动第一期肃正战
第一阶段自1939年1月至5月;第二阶段自1939年6月至9月;第三阶段自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
为强化华北地区的军事整肃,日军于1938年11月在山东设立第12军,该军统辖驻防苏北的第21师团、驻守鲁南的第114师团,以及由华南战场调来的第5师团(驻防青岛)等部队。同时,将华中战场的第27师团北移,部署于河北省东部,以天津为中心,沿北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北段地区展开部署。在第一期肃正作战中,华北方面军指令第12军全力肃清鲁北道以及胶济、津浦两条铁路沿线的敌军。第27师团的职责是,以主力部队清剿津浦路西侧的敌军,并分遣一部至津海道南部的津浦路东侧区域,以支援第12军的行动。德县(今德州德城区)和陵县(今德州陵城区)正处于第27师团与第12军第5师团防区的接合部。第5师团作为日军的重要作战力量,担负着关键的战略任务。历史最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支战斗力最为强大的王牌师团之一,该部队曾对中国军民犯下了无法洗刷的罪行。因其第19任师团长、广为人知的板垣征四郎中将,此师团亦被世人称为“板垣师团”。在1939年4月的大宗家战斗爆发之际,担任师团长的是今村均中将。依据肃正作战计划,该师团的第5骑兵联队的一个骑兵大队被部署在德县地区。自1939年2月起,这支骑兵大队依托于第27师团,承接了“南”号作战计划后续任务,并在津浦线以西地区执行肃正和警备任务。
八路军进冀鲁边
冀鲁边区,地处山东省北部与河北省东南部的接壤平原,东西绵延约125公里,南北跨度将近250公里,其地理位置直接钳制着天津以及津浦铁路的北部线路,因此,日军对该地区给予了极高的重视。1938年夏日,八路军115师第5支队(该支队由团级编制,以343旅685团2营为骨干,经过扩编而成)与129师津浦支队一同从冀南挺进,进驻冀鲁边区的乐陵、宁津等地,成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中心展开了英勇的抗敌斗争。
为强化冀鲁边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遵循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指令,1938年9月下旬,115师343旅政治委员萧华率领旅机关及补充团的部分干部,共计百余人,从山西踏入山东省乐陵县。同年10月,冀鲁边地区的八路军部队进行了整编,正式命名为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其下设有第5支队、第6支队以及津浦支队。至1939年3月,第5支队晋升为旅级编制,原下辖部队经过整编,成立了第5团;禹城县的地方武装并入,组建了第4团;冀鲁边区地方联合自卫武装的第18团则改编为第6团。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崛起,对天津日军及津浦铁路线构成了巨大威胁。在第一期肃正作战中,华北日军加紧了对该边区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和“扫荡”行动。1939年1月,日军集结了驻山东、河北两省的第5、27、114师团部分兵力以及当地伪军共计2万余人,分别从济南、沧县、德县等地出发,对盐山、庆云、乐陵等冀鲁边区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了合力“扫荡”。面对此情势,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果断撤出乐陵,分散兵力与日伪军周旋。我5支队先后三次攻克灯明寺、支援18团、伏击魏龙江、夜袭李元寨,接连取得胜利。日军对此十分恼怒,四处搜寻我军主力,企图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华,八路军5支队支队长。
曾国华所指挥的5支队伍及其下辖的5团(其中第2营由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领,在利津、沾化地区独立行动),于1939年3月27日抵达陵县东部的大宗家地区,进行短暂的休整,停留了三昼夜。第三日晚间,他们搭建戏台,上演戏曲,与当地军民共同庆祝胜利。然而,5支队的这一番热闹场面,却被德县日军派遣的情报人员察觉。日军初步推断,大宗家地区的部队系“八路军特别纵队”及其下属的第5支队,兵力多达数千人(日军记录中标注为3580人)。此外,情报还揭露了5支队曾参与平型关大战,痛击日军第五师团的辎重部队,导致“不可战胜的皇军”遭受重创,面子扫地,日军对此怀恨在心。这场即将到来的血战,无疑是一场狭路相逢、仇人相遇的较量。但实际上,5支队在大宗家地区的兵力仅有1700余人。显然,日军为了彰显自身部队的勇猛,夸大了对手的兵力,这也暴露了日军情报工作的不准确性。
支队机关、直属骑兵连、特务队以及5团3营的11连,总兵力约500人,由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参谋长刘政和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共同指挥,驻扎于大宗家东南的前后侯家村。5团团部、特务连和3营12连,共计约400人,由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特派员谢甲树领导,驻守大宗家。5团1营,约有500人,由团政治处主任朱挺先、1营营长温先星、教导员唐文祥率领,驻于大宗家东北的赵玉枝家。该村北部有一道约二至三米深的壕沟,直通大宗家的旱河。此外,5团3营营长马宗凯带领的9连和10连,驻扎在大宗家南部的阎福楼。
当时,如此安排兵力部署,主要基于地形考量。前后侯家南地势开阔,我方仅需少量兵力便足以封锁来犯之敌。而赵玉枝家北侧则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此地为敌军潜袭或我军转移提供了理想的掩护。鉴于此,我军的主力部队便驻守在赵玉枝家附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战斗在拂晓打响
为确保对八路军第5支队的全面侦察,日军第5师团的骑兵大队携手步兵某联队的一个半小队、野战炮兵第5联队第8中队的一个小队,以及兵站汽车某中队的一个分队,共计416名官兵,组成了先头部队。该部队于3月31日晚(按日军资料记载为4月9日),自德县驻地进行出发,向陵县东部地带进发。与此同时,日军还从德县、商河、临邑、东光、盐山、平原等地抽调了800余警备部队作为后续增援力量。至此,日军投入战场的总兵力约达1200余人。翌日4月1日凌晨(日军资料中记录为4月10日拂晓),日军部队逐步逼近大宗家地区驻扎的八路军。骑兵大队长山田大佐敏锐地察觉到此时八路军警戒处于极度疲惫与疏忽状态,认为这是进攻的绝佳时机。
据此,他依照分进合击的战术意图,以本部两个中队为核心,将所有参战兵力划分为三路纵队,依次推进,持续扩大搜索范围。敌先头骑兵约70余人,在距大宗家村南约二至三里的沙丘旁驻足,随后绕至赵玉枝家与尚家庵之间的沙丘地带,作为机动援军。敌步兵则分作两路纵队,直插大宗家与侯家之间,尔后左右分散,犹如两条毒蛇般将两村紧紧包围,并逐步缩小包围圈。拂晓时分(日军资料中记录为上午9时许),日军各纵队已全面展开,于×场店、侯家、大宗家一线设立阵地,并针对遭遇的八路军部队发起了猛攻。
日军突袭迅猛,出乎我军意料之外。驻守大宗家的哨兵率先察觉敌情,5团团长龙书金迅速组织部队奋勇抵抗,团政委曾庆洪随即向支队汇报敌情。支队长曾国华在听到枪声并接到报告后,发现敌人已将大宗家和侯家重重包围,且电话线已被切断。他立刻意识到形势严峻,部队陷入困境,此时求援已无望,唯有各自为战。曾国华一方面组织支队机关、警卫和通信分队进行阻击,另一方面派遣通信员火速通知大宗家的5团团部和赵玉枝家的5团1营,要求他们保持冷静,节约弹药,坚持至夜幕降临再进行突围转移。他坚信,由龙书金、曾庆洪率领的红5团定是坚韧不屈的硬汉、锋利无匹的利刃。而被分割在敌后的我3营阎福楼部,也遭遇日军迂回包围,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龙书金,八路军5支队5团团长。
首当其冲的大宗家,团长龙书金率领特务连及3营12连的勇士们,在村头、院落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近身肉搏战,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特务连战士人手一把大刀,与敌人展开了逐屋逐院的殊死搏斗,连长李东海身先士卒,勇猛异常,连砍数名日军士兵,但在激战中英勇捐躯。5团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在团特派员谢甲树的指挥下,也纷纷投入了战斗。那些原本手持厨具、医疗器械的炊事员和卫生员,纷纷拿起牺牲战友的武器,操起扁担、菜刀、铁铲,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大宗家内外充斥着杀伐之声,村头村尾、院落巷道,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侯家村中,曾国华、王叙坤等支队领导隐蔽于一堵低矮的墙后,既指挥战斗,又研讨对抗敌人的应急策略。他们决定先削弱敌人的骑兵力量,一旦骑兵被击溃,步兵也就易于对付。赵玉枝所辖的1营接到指令后,营长温先星率领数个连队,采取弧形阵型,宛如坚固的铜墙铁壁,向尚家庵村西的沙丘底部发起攻击。当距离敌人仅数十米时,1营的机枪与步枪齐射,手榴弹如雨点般投向敌群。日军的骑兵陷入混乱,匆忙迎战。一时间,沙土飞舞,天色昏暗。战士们手持锋利的刺刀,向日军骑兵的马腹猛刺,军马发出悲鸣,狂嘶不已。支队领导听到大宗家村北沙丘一带杀声震天,人喊马叫,得知5团1营已与敌人骑兵交火,随即命令支队直属骑兵连出击,与1营并肩作战。骑兵连长接到命令后,在马上吹响一声口哨,战士们迅速上马,形成一字形阵型,手持闪亮的马刀,向村外冲去。包围侯家的日军措手不及,未曾料到八路军还拥有骑兵,纷纷四散奔逃。我骑兵突破重围,直冲沙丘。如此一来,骑兵连与1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日军骑兵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在附近枣林中督战的日军大队长山田大佐,见其骑兵陷入困境,便站在高处挥舞着膏药旗,用旗语指挥包围侯家的日军火速增援。我1营特派员高子桂发现枣林中有日军指挥官,立即命令2连1排,以沙丘和枣林为掩护,迂回至敌人后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突袭。一排手榴弹投掷出去,山田大佐及5名日军指挥官当场被击毙,其肩章、证章和指挥刀被缴获。混乱过后,日军迅速更换指挥官,调集兵力,再次向我军发起猛攻。战斗正酣,1营与日军在邵家坟地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但多次进攻均未成功,损失惨重,5团政治处主任朱挺先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血战终日
4月1日晨,大宗家战斗依旧陷入紧张状态,随着日军援军的接连抵达,战局对我方愈发严峻。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以及特派员谢甲树各率部下,巧妙选择有利地势,奋勇抗击日军攻势。面对来势汹汹的密集敌军,龙书金指挥若定,沉着冷静,英勇果断。他指挥12连战士,巧妙利用村庄四周的墙壁、树干、猪圈和厕所等天然掩体,以猛烈的火力有效遏制了敌人的进攻。
在侯家村,支队长曾国华闻悉敌方指挥官已遭击溃,便趁胜指挥支队机关撤离至村外。警卫、通信分队以及机关干部均投身一线,全力实施突围。他即刻派遣通信员传令部队切勿恋战,迅速撤退。然而,大宗家已被敌军严密包围,难以实现即时撤离。当日军将攻势集中在大宗家和侯家村时,南部的阎福楼3营的10连趁机突入大宗家,支援团部。团长龙书金与政委曾庆洪随即率领12连和通信排巧妙迂回至村北的洼地,与来势汹汹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缠斗。此刻,大宗家我军坚守的村内地盘上充斥着敌军,而野外进攻的阵地则是我军阵地,敌我交错,杀伐声此起彼伏。村内的特务连与3营的10连在7、8个小时的激战中,面对缺水断粮的困境,与敌人进行了30余次的激烈交锋,书写了我军攻防战史上的辉煌篇章。然而,我军伤亡惨重,双方展开了近距离的肉搏战,逐屋逐房地进行争夺。面对日军凶狠野蛮的进攻,八路军战士更是展现出了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
激战持续至午后三时,我方仍牢牢掌控着大宗家阵地。敌方不断增兵,甚至调来了野战炮,局势愈发紧张。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被围困在村中的团机关和特务连、第十连被迫退守至大宗家村内的一座被誉为“保险院”的建筑。这处建筑属于一位年逾古稀的爱国地主宗子敬,他的宅邸深藏于青砖水泥砌成的围墙和高耸的角楼之中,宛如一座坚固的城堡,深受村民的赞誉。第五团的战士们迅速占据了“保险院”的有利地形,将机枪安置在四个角楼和围墙的垛口,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对日军进行猛烈的火力打击。日军也纷纷爬上附近的土屋,向大院发起猛烈的射击。在我方弹药告急之际,宗子敬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藏于后院马厩内、专为防盗护院而准备的十几箱枪弹,犹如一场“及时雨”。有了这些宝贵的枪支弹药,战士们士气大增,战斗力倍增。他们迅速击退了进攻的日军,但“保险院”依然被敌人重重包围。据日军资料记载,在合围行动启动后,“右翼(赵玉枝家方向)及中央纵队(侯家方向)的战斗进展顺利,成功突破敌军多道防线;左翼纵队(大宗家方向)因敌军依托村落进行顽强抵抗,进展并不顺利”。

黄昏之际,我军与敌激战正酣,难分胜负。支队长曾国华为保留我方实力,果断下令5团迅速撤离战场。龙书金接到撤退令后,即刻派遣通信员通知村中部队,然而不幸的是,所派通信员均在途中英勇牺牲。村中尚有5团机关、特务连及10连,正遭受敌人的严密封锁。曾庆洪遂决意亲自调遣赵玉枝家的1营支援,尽管他并未意识到1营此时亦遭受重大伤亡,且已被敌军阻断。日军目睹八路军阵地中突然涌现数人,密集的枪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曾庆洪等英勇战士不幸中弹倒地。政委的英勇牺牲,激起了5团全体指战员的满腔怒火,他们誓言与敌人殊死一搏。
“右侧及中央纵队在大宗家布下包围圈,并展开进攻,逐步将敌人驱入圈内,至17时30分,成功包围并歼灭了敌军主力。”
与此同时,邻近村落中的部队亦纷纷成功突破重围。为抵御敌人可能的再度围剿,曾国华率领支队总部及第五团的剩余部队,途经赵玉枝家东北的高家庄,横渡大宗家旱河,最终抵达德平县义渡口进行休整。随着血色晚霞的降临,大宗家的战斗逐渐落幕。
双方伤亡与战果
在大宗家战役落幕之际,双方在伤亡统计上存在着显著的分歧。根据日方提供的资料——仅记录了骑兵大队的战绩,而未包括增援部队的情况——数据显示:日军方面击毙八路军700人,俘虏53人;而自身则战死10人,负伤31人。在我方各类资料中,5团团长龙书金因负伤致残、团政委曾庆洪、政治处主任朱挺先、团特派员谢甲树牺牲的信息是一致的。然而,关于歼灭日军的具体人数,却存在“300余人”、“500余人”、“700余人”等多种说法;而自身总损失则有“伤亡500余人”、“伤亡400余人”、“牺牲400余人”、“伤亡300余人”等不同的描述。应当指出,在战时,为了鼓舞士气,双方都会有意夸大对方损失,而缩小自身伤亡。从日方资料来看,参与行动的兵力总计416人,却对大宗家地区的八路军3580人发起了偷袭,仅以41人的伤亡代价,便成功包围并歼灭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近五分之一,并予以驱逐。这一战绩显然有夸大之嫌。此外,战斗是在平原村落展开的,八路军依托村落的院墙进行防御,对抗以骑兵为主的日军,双方在一天内展开了拉锯战,我方击毙日军军马100余匹(日军只搬运人尸,不搬运马尸),可见攻方的损失亦不会轻微。至于我方,由于当时对外公布的战报中,歼敌数一般会加倍发布(1944年3月军委电令各军区禁止),再加上此次遭遇突然袭击,匆忙进行防御和突围,最终并未能完全控制并清扫战场,因此歼敌数据的准确性难免存在夸大。至于自身损失,关于“伤亡”与“牺牲”的描述也存在着混淆和矛盾之处。

杨成武将军亲笔题写的“大宗家战斗纪念碑”。
敌酋山田大佐遭击败后,日军并未立即将他的遗体运回德县,而是选择在大宗家东张丰池村的一座小庙内将其火化,并将其他阵亡的日军暂时安葬于此,之后方才将其遗体移走。1940年10月,日军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亲自前往庆云县至沧石公路,迎接即将从石家庄南下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大将。在山田大佐的墓前,本间中将特地拜访,明确表示:“此地正是山田大佐及其众多部下在激战中英勇捐躯之所。”若仅阵亡十人,恐难以唤起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的深切缅怀。综合分析,此战日军伤亡人数应接近三百人。
八路军第五支队虽最终成功实现突围,然而损失惨重,尤其是主力团第五团,该团在抗战期间经历了最为惨烈的战斗,牺牲尤为惨重。战事结束后不久,5支队便将第四团并入第五团,旨在重振第五团的士气与实力。根据乡亲们的收殓情况及部队的整编情况分析,大宗家战斗中我军共有1700余人参战,伤亡人数估计达到半数甚至更多。
鲁北战场上的大宗家战斗,堪称抗战时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同样在八路军的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双方伤亡悬殊,但此战无疑是真金不怕火炼的血战、恶战。尽管我军伤亡惨重,却依然重创了日军,有效遏制了侵略者的狂妄气焰。我军成功突围,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驻冀鲁边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狂妄企图。据传,此战也令日本当局震惊,东京甚至进行了广播报道,并对山田大佐的陨命表示哀悼。
在战后休整期间,曾国华于连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大宗家战斗进行了深刻总结。他首先强调,大宗家战斗是在敌强我弱且遭遇敌军突袭的不利形势下,5支队被迫发起的一场激战。这场战斗是对日寇精锐师团的殊死搏斗,虽痛击了敌人,却也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随后,他沉痛地归纳了四条教训:一是因连续胜利而滋生轻敌麻痹心理,正应了“骄兵必败”的古训;二是违背了游击战术的原则,犯了“久驻一地易遭敌袭击”的兵家大忌;三是驻守新区时未能布置周密的情报工作,导致“耳目闭塞”的困境;四是未预先制定应急作战方案,以致陷入“仓促应战”的被动。曾国华的总结与自我反省在部队中激起了强烈共鸣,部队由此知耻而后勇,5团这支老红军部队迅速焕发出新的战斗精神。在随后的抗战岁月里,5团挺进鲁西,愈战愈勇,成为冀鲁豫根据地的“铁拳”,后发展演变至沈阳军区陆军第16集团军步兵第46师136团。
倍悦网-配资官方网站-配资炒股技巧-正规在线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